|
一默如雷
——评崔自默著《为道日损——八大山人画语解读》
张帆(北京大学教授)
三百年的沉默
1684甲子年后,朱耷始称“八大山人”。他不再说话了,大书一个“哑”字贴在门上。这一沉默蓄积着极痛烈而深刻的许多伤害,如巨石竭泉,火遇湿絮,隐闷而不能出。这饱含巨大力量的委屈是等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然而三百年过去了,人们都只看他的泪点,同情他的身世,猜度他的仇恨,窥探他的癫狂。肤浅乏力的一片嘈杂让这沉默更深地埋藏起来,暗涌如雷。直待崔自默先生断然言说:“靠被同情是成就不出大师来的。八大内心固有深不可测的痛楚,但若仅以‘墨点无多泪点多’、以‘天地为愁,草木凄悲’视八大,那就恐怕脱不了皮相之判,‘艺术之伟大不仅仅在表现内心的痛苦,而更在化解这痛苦。大艺术最终是对灵魂的大慰藉,从大牢笼得大自在’。从八大的画中看出‘泪点’来,乃是循着遗民普遍有着的沉闷愤慨之情而立论,非为无由;但研究八大津津于斯,则浮于笔墨之表象,失之矣。”八大山人的血统、追求、造诣都是非常独特的,正是这一独特造成了从者甚众,而知者寥寥,解家多而方家少,所以喧嚣之中仍是沉默。今有崔自默先生这一解,解出雷霆万钧,使生命回到本真,争论回到正途。
八大山人, 到底是谁
借助历史,我们可以不止一次地活在:此时、此刻和昨天。可以沉浸在那些确实活过,那些在活着的时候就面对过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并为此而挣扎求索的人们的亲身体验中。在这些体验中,学者和读者有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和疑问,而一个优秀的学者是从他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发现过去的问题。历史思维的决定性问题是:我们是谁?历史的叙述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答案的深度直接取决于回答者的高度。
《为道日损》第一章,崔自默先生完成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心理史学。八大山人的历史资料是极其有限的,而他的一生又是如此的跌宕奇诡。只有从心理入手,才能真正的理解和描述作为艺术家和一个敏感男人的八大,这两点如果割裂都是很难说清楚的。八大山人首先是个敏感的男人,然后才成为艺术家。崔自默先生首先意识到了八大山人独特的心理建构,进而指出了这种心理建构如何在中国宣纸上的实现,从而给出了这一个艺术家的独特而本质的路径。崔自默先生在关键事件上严守具体史实,具体而微,另辟新径从八大山人的印、款、题诗入手,原来许多令人困惑的词语被他从《诗经》、从《列子》、从《朱熹集注》里找到源点,解读出来。微观研究大大开拓了研究的领域。历史是一个个故事,故事是一个个人讲的,所以没有真正的历史真实,所有的是信服度。信服度不在于史料数量的繁冗、细节的真实,而在于与历史、与人物接近的距离。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要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所反映的生命其实正是叙述者本身的精神力量。历史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对历史解释的精神支撑,考察历史与窥探隐私又究有何异?理解一个艺术家只是评论他的必要条件,艺术家都是沉浸其中的,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创造,而评论家必须环顾左右才能看清自己的对象。我们可以说八大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对他评论的歧义,接受儒家的人看到了入世,接受道家的人看到了自然,接受佛家的人看到了悲悯,不能说他们看错了,只是不全面。其实这一切都属于八大,只有同样都理解这些的人始能全部看到。我们可以说这些人都在仰视八大,而崔自默先生是在旋转中以各种角度在审视八大:“儒家的信条根深蒂固地左右着八大的生存观念,道家的方法随时随地地启发着八大的处世方法,而佛家的思想则具体而微地影响着八大的艺术模式。”
崔自默先生第一个高声断言:“八大山人是执中庸之道的仁人君子,他无心做怪,所以称圣。”这个独立的发现过程是从“遮蔽”到“去蔽”的过程,是“为道日损”的过程。发现者的人格强度和生活方式是理解的关键。与其说他发现了八大山人最深刻的人格秘密,不如说这秘密他本身就有,所以崔自默先生从来就知道,他与八大山人在生命的意义上同构:“如果说他最终还有痛苦的话,那便是他无论如何也挣脱不掉的儒家责任感。这是人类共同的大挂碍,追求大美与传达大美对他而言举足轻重,否则生亦如死。”当我读完这段话后,不禁掩卷而思。就是这些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声音与我的生命相遇,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把那些汲取出来的理解存放在我的心灵之中,我就不再仅仅是我自己,而变成了与历史中那些杰出灵魂缠绕在一起的指向无限的一个“成人”。所以我爱着,像爱生命一样爱着这些大美之言。
学术的深厚与美的灵动
崔自默先生的书著为艺术史人物研究创造了一个学科模型。那就是使其不再局限于美学范畴的历史研究,而尽可能地吸纳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史学、文献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符号学、比较学、心理学等等,按一定顺序,逻辑辩证地从各个维度复活、勘定历史人物和阐述艺术。如果说一个学科模型的建立还是相对容易把握的,那么丰满它血肉的人就需要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独特的理性思维、深邃的学术眼光、系统的专业建树、穿透学科界限的悟性、参晓古今的学养与慈悲。
《为道日损》一书是严格的学术著作,其注释的数目是创记录的:1315处,书长275页,平均每页5处注释;涉及古今中外510多位名人,550多本文献书目。当这些人名和书名在你面前一一掠过,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养眼而愉悦的过程。这些注释并不是非引用不可,它们更像一个个文化的引桥,崔自默之所以尽可能地列出这些开阔而实用的智慧文字,只是为了读者更好、更快、更入骨地懂得艺术带给我们的喜悦。就像那个被大话了的唐僧,唠叨的背后全是悲悯,只为众生的受用与觉悟。文化是活着的,并将永远活着,文化的生命力就在这无私的薪火相传中。
学术著作的阅读一般来说即便对于专业人士也是一个枯燥乏味而略显艰苦的过程。崔自默先生的著作读起来却令人愉悦,那灵动的文字和处处可见的禅锋使人欲罢不能,即便是非专业人士读之也颇有益处,而这一点就不是一般所谓的学者能做到的了。这文字的愉悦,却又不能带来阅读的轻松,阅读此书恰似在中国文化高原上散步,没有体能和储备你是做不到的;一旦你上去了,风景就是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观照,八大山人和崔自默合筑成的这种观照,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极致,是不可替代的。你怎么可能错过这种观照呢?
艺术及艺术评论的重要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病态的,人的存在被裹挟在社会机器这个庞然大物中,失和于己。人的惯性化生存,空泛语言的沉沦,跟风逐流,在同一理论模式填充材料,注经式的学术研究制造了无数文化垃圾,滋养了太多文化蛀虫。相信有一天,我们会从喧嚣中醒悟过来,当我们为此懊悔而蒙羞的时候,再回过头看看崔自默先生独立审慎的文字,看看他如何把八大山人的沉默解放为沧桑正道的漫天惊雷,就可以更正确的认识崔自默和崔式之学的价值。
于无声处,一默如雷。
2007年12月
//////////////

崔自默博士与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张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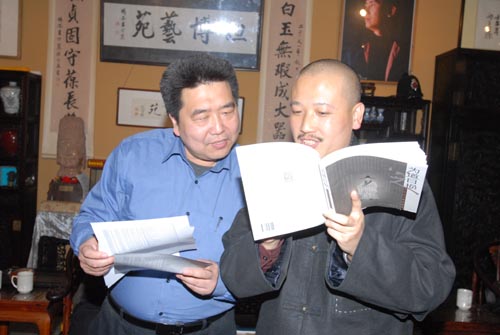
北京大学张帆教授与崔自默博士交流关于<为道日损>一书的学术细节

北京大学张帆教授撰文<一默如雷>评论崔自默的<为道日损>一书

北京大学张帆教授与崔自默博士交流
总共1页 1
|



